“啊,杜公是你,怎么会到这里来的?”寺里的当家和尚赞公是杜甫的朋友,虽然皈依佛教,可依然关心国事。一见杜甫,惊诧地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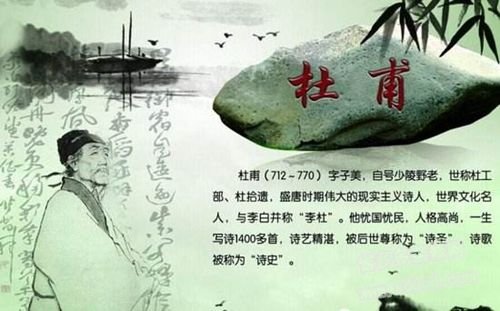
“这几天长安街头,叛军成群结队,高唱夷歌,开怀痛饮,情况异常, 不知道战事怎样,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?”
“听到一个极坏的消息,官军又打了一个大败仗。潼关失守以后,皇上派房公(房琯)率兵收复两京(长安和洛阳)。房公虽有报国之心,可是没有作战经验,他把军队分成三路进攻。十月二十一日,中路和北路全军覆没,四万土兵的鲜血染红了陈陶泽。得胜回长安的叛军,箭不都是像用鲜血洗过一样吗?那是四万义军的鲜血啊!”赞公沉痛地说。
“叛军箭上沾着的,不仅是四万义军的鲜血,也包含那些被无辜杀戮的人民的鲜血,那些自动组织起来反抗、斗争的英雄的鲜血!”杜甫的眼睛里冒着仇恨的火焰,愤怒地说。原来自从长安沦陷以后,人民经受不住胡人日夜的摧残、骚扰,就自动组织起来反抗,这里扑灭了,那里又起来。杜甫亲眼看见一队胡人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匆匆在大街上走过,只见那青年神态自若,面不改色,大声说:“杀头吧!反抗的人民是杀不完的!乡亲们,组织起来打击胡人!胡人的日子不会长了,官军就要来了!”人们都激动地含着泪水,痛心地说:“又一个英雄倒下了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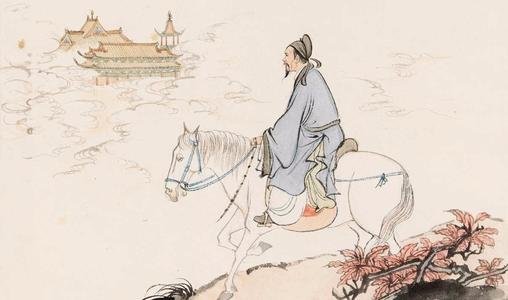
这天杜甫回到住处写了有名的《悲陈陶》:
孟冬十郡良家子,血作陈陶泽中水!
野旷天清无战声,四万义军同日死!
群胡归来血洗箭,仍唱胡歌饮都市。
都人回面向北啼,日夜更望官军至。
两天以后,杜甫又听到一个消息,说陈陶泽败后,房琯(guan)持重不进,但是监军的宦官一再催促,房琯率南路军再战,在咸阳西南的青阪又大败。
杜甫心情无比沉重:“我军损失太重了! 人民虽然渴望官军,但反攻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行啊。”
冬天过去了,春天又来了。当年繁华热闹的长安城里却是杂草丛生,人烟稀少,一片凄凉景像。

杜甫身陷贼中已经第二个年头了。他双目深陷,面容瘦削,头发一下子全白了——他头发本来稀少,由于不断爬搔,现在差不多连簪也戴不住了(古人男女都留有长发,男的将发盘于头顶,用簪簪着)。自从唐军在青阪战败以后,他不大听得到战事的消息了,这就使他更加担忧时局。他也怀念着远在鄜州的妻子儿女——前些日子他曾偷偷地给妻子寄过一封信,寄出以后,日夜盼望,可是至今没有回信。他是多么盼望收到一封家书啊!


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